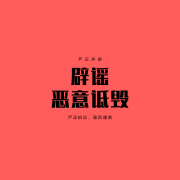(一)
3月27日凌晨四点,这个城市还在沉睡。
阿华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悄悄地抵达考场附近,开始按照事先协商好的范围权限布置现场。
这一天,是陕西省省考的日子。考点附近是大片的居民区,阿华他们脚步很轻,生怕影响了其他人休息。几个伙伴训练有素地将提前准备好的kt板固定在事先跟城管物业都沟通好的位置,分配传单和《省考蓝皮书》。蓝皮书是几个导氮陕西考区的教研老师运用专业能力总结出来的精髓考点,考前看上几眼,就能再多拿到救命的几分。阿华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义。
年纪最大的于姐不声不响地走过来,递给阿华一盒金嗓子喉宝。这是每次打现场都少不了的法宝:一天下来,基本要全力以赴地咆哮四五个小时,谁的嗓子都吃不消。但是阿华他们都习惯了。
因为咆哮,才是导氮。
很多友商觉得导氮咆哮是为了哗众取宠,夺人耳目。但阿华他们知道,导氮人的咆哮,是因为年轻,因为激情,因为活力,因为热爱。他们的咆哮,一定能让在考公路上拼搏的同龄人感受到振奋和鼓励。对每一个导氮人来说:
导氮的咆哮,是一种态度。

(二)
今年,是岑兰考公的第三年。也是她作为应届毕业生参考的最后一年。
作为985的金融本科毕业生,岑兰的同学要么考研要么就业,像她一样依然在执着考公的,已经寥寥无几。就连她的父母,也不像刚毕业那年那样热情地鼓励她参加国考、省考、三支一扶。很多次,父母在餐桌上都有意无意地说起“别人家”的孩子。她知道,那个曾经考上985,让父母骄傲的姑娘,正在一次一次无功而返的公考过程中,成为父母的“难言之隐”。
她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参加考试了。她只知道第一次参加国考笔试的时候,父亲亲自把她送到考场,然后在一直等到考试结束接她回家。而这一次,她出门时喊了一声“我走了”,都没有任何人回应。
岑兰一个人走在路上,觉得自己格外孤独。三月的天津,春天的风还是有些凉的,又赶上扬沙天气,灰蒙蒙地让人窒息。
这是最后一次吧。她想。如果还是考不上,就随便找个工作。梦想什么的,有时候在现实面前,真的一文不值。一个人的踯躅独行,真的好累。
远远的,岑兰听到一群人举着牌子站在路边高喊。她知道,那是导氮教育的老师们在现场宣传咆哮。这些人好像永远不知疲惫,有时候听到几个人嗓子都喊破了,也还是继续声嘶力竭地坚持着。
跟导氮的老师越走越近,岑兰不自主地加快了脚步。考生们大多三两成群,只有她是一个人,她觉得很不自在。就在这时,她第一次,听清了导氮人的口号,那几个人喊的是:“导氮教育,祝大家成功上岸!”
岑兰愣了一下。多久了,她没有收到过任何人的祝福。就连自己的父母,也都在劝她放弃。这一次,她所渴望的祝福,却来自一个路边的陌生人。
或许看到了她的关注,一个穿着导氮马甲的小哥哥立刻走上前来,热情地递给她一本小小的蓝皮书,告诉她:导氮今天有四场公益直播,教给大家快速提分的技巧……岑兰有些茫然的看着这个嗓子沙哑的陌生人,耳边回荡的,是那句最暖心的:一定要加油哦!导氮教育,祝你成功上岸!!
岑兰的心,忽然有些暖。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了。考不上算什么,这次真考不上,就去报个导氮的培训班,继续考。她觉得:
导氮的咆哮,是一种陪伴。

(三)
佳佳出门的时候,儿子还没醒。
佳佳着急地扒了几口饭,简单跟母亲交待了几句,带着歉意出了门。
佳佳今年33岁了。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年龄还奔走在考公的路上非常尴尬。但是她没得选。丈夫的出轨让她不得不独自承担养家糊口的担子。父母年纪大了,儿子刚上小学,她需要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让这个家有足够的安全感。
公考的年龄限制是不超过35岁,佳佳只有3年的机会。但是她不想报辅导班。倒不是心疼钱,她只是不想跟那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在同一个教室、同一条起跑线上一起开始学习。她觉得特别难堪。就连去考场,她都有意无意低着头,躲避着周围人的目光。
临近考场,她的头垂得更低了。然而过马路抬头看车流的刹那,她却不自主地被对面一个教育机构的老师吸引了目光。
那是一个看起来比她还大几岁的中年女性,高高地站在石墩上,正在激情饱满地向现场学员讲解高频考点和紧急得分技巧。佳佳情不自禁地聚拢过去,挤在人群里看着这个年近40的女讲师。她声音洪亮,讲解清晰,即使不用小蜜蜂之类的扩音设备,也一样能让方圆30米之内的考生听得清清楚楚。在佳佳眼里,她看起来那么斗志昂扬,咆哮的样子整个人都在发光。
不知不觉的,佳佳悄悄挺直了腰杆。她不知道是女讲师讲解的知识点给了她信心,还是对方昂扬的斗志给了她力量。总之,佳佳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了。
她特意认真看了看女讲师身后的宣传牌:导氮教育。佳佳默默把这个名字念了几遍,在她看来:
导氮的咆哮,是一种鼓励。

(四)
导氮的咆哮,似乎一直是同行眼中的“另类”。导氮却始终在各种讥讽和质疑中一路咆哮下来,相信,未来也会坚定不移地一路咆哮下去。
因为在导氮人眼中,咆哮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特立独行,咆哮是导氮人对工作和人生的一种激情蓬勃的态度,是对考生们无形的鼓励和陪伴。
咆哮,是导氮人热爱的方式。